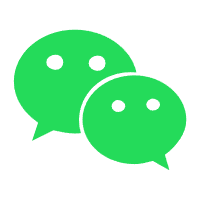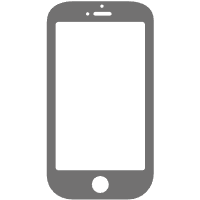风险投资中的估值调整协议:法律效力的争议与实践
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已成为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成长的重要金融工具。作为投融资双方达成交易的核心条款之一,估值调整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简称VAM)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该类协议通常以“对赌协议”形式出现,旨在根据目标公司未来业绩表现对初始估值进行动态调整,从而平衡投资方与创始股东之间的利益。然而,随着相关案例的不断涌现,其法律效力问题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焦点议题,尤其在涉及股权回购、现金补偿等具体执行路径时,法院裁判标准呈现多元化趋势。
估值调整协议的典型结构与法律性质界定
估值调整协议一般包含若干核心条款,如业绩承诺、未达标情形下的股权回购义务、现金补偿机制或股份补偿安排。从合同法角度分析,此类协议本质上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其生效前提是特定未来事件的发生,如企业净利润达到约定指标。尽管部分条款可能带有明显“保底”色彩,但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缔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原则上应认定为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1347号案中明确指出,若对赌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情形,则可依法认定其具有法律效力。这一判例为后续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司法实践中对“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标准
近年来,各地法院在审理涉及估值调整协议的纠纷时,逐步形成了以“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与“维护公司法人独立性”并重的双重审查标准。例如,在(2017)京民终685号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当对赌协议仅约束投资方与原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且不直接导致公司资产减少或注册资本变动时,该协议并不违反《公司法》第35条关于“不得抽逃出资”的禁止性规定,因而具备法律效力。反之,若协议要求公司本身承担回购义务或提供担保,因可能影响公司偿债能力及外部债权人利益,往往被认定为无效。这一区分逻辑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商事自治与公司治理秩序之间平衡的审慎考量。
涉及公司作为责任主体的对赌协议效力困境
在实务中,不乏投资方将目标公司列为对赌义务主体的情形,即要求公司在业绩未达标时履行回购义务或支付补偿款。此类安排虽在融资谈判中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极易触碰法律红线。根据《公司法》第35条和第142条相关规定,公司不得随意减资或向股东返还出资,否则构成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破坏。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再379号案中进一步强调,若对赌协议实质上构成公司向股东返还投资款的行为,即使名义上由公司承担义务,亦应视为变相抽逃出资,故该部分条款无效。这一立场表明,即便协议文本表述清晰,一旦涉及公司作为履约主体,仍可能因违反强行法而归于无效。
不同行业与投资阶段对协议设计的影响
估值调整协议的适用性并非一成不变,其法律效力还受到行业属性、发展阶段以及投资轮次的影响。在早期科技创业项目中,由于盈利模式尚不清晰、现金流不稳定,投资方更倾向于设置高门槛的业绩对赌条款以锁定预期回报。然而,此类设定在司法实践中更容易被认定为“显失公平”或“加重一方责任”,从而引发效力争议。相比之下,在成熟期企业并购重组中,对赌条款多聚焦于收入增长率、市场份额等可量化指标,因其具备较强可验证性,法院更倾向于认可其合理性。此外,红筹架构或跨境投资背景下的对赌协议,还需考虑域外法律冲突与仲裁管辖等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
律师实务建议:如何规避法律风险
基于上述司法裁判趋势,律所建议在设计估值调整协议时采取更为审慎的结构安排。首先,应避免将公司本身作为对赌义务人,而应确保责任主体限于创始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其次,可引入分期履行、比例调整等柔性机制,降低极端情形下违约后果的不可控性;再次,建议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权”等条款,并辅以尽职调查报告与股东会决议作为支撑文件,增强协议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对于存在境外投资背景的项目,宜提前规划争议解决机制,优先选择国际仲裁机构进行管辖,以提升执行效率与法律确定性。
典型案例解析:某生物医药企业对赌纠纷的判决启示
以某知名生物科技公司为例,其在完成A轮融资时签署了包含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30%的对赌协议。因受疫情冲击及研发周期延长影响,企业未能实现业绩目标。投资方随即要求公司按约定回购股权,金额高达数亿元。该案经地方中级法院一审后支持了投资方请求,但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协议中关于公司回购义务的条款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资本维持的原则,且未经过法定减资程序,最终裁定该部分条款无效,仅支持创始股东个人承担回购责任。此判决不仅明确了公司不能成为对赌义务主体的基本底线,也为后续类似案件确立了清晰的裁判指引。